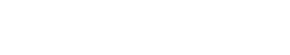起义军在普宁
发布时间:
2019-02-24
这里收录的是陈公培给普宁县修志委员会的信,说明八一起义军在普宁的活动情况如下:
普宁县修志委员会负责同志:
十月十九日您会来信早经收到。因为我近时作点研究工作,有大批文件要看,所以不能专心思考三十五年前的事,而且本人不仅事前事后都不曾到过普宁,而且也不曾到过东江一带,所以有些地理情况也不清楚。譬如流沙这一地名在一般地图都找不着,也不易得到资料帮助回忆。事实上,我当时的情况也颇特殊,除了在汕头作过三、四天贺总部留守(任务觇定也不明)外,两个月中间一直没有具体实际的职务,只是贺总部的一个特别随行人员,因此对党、政、军三方面的事情都不太摸得清楚。离开汕头后,我的留守职务,自然解除,而恢复随行状态,因此极难有全面了解,纵然可以回忆出一些脑筋中的零星映象,恐怕也不足供您会修志参考。
但是既承您们询问,我因此只能就来缄所提两点问题,就连日思考所及,作一简略的答复,也只是一个初步粗糙回忆而已。
(一)“流沙会议”
在流沙,个人记得有一次“事关重要的会谈”。但这一次会谈在党史或革命军事史上是否算作一次“会议”,我个人还没有看见这样的记述,因此,称一次“会谈”为“会议”似乎还值得考虑。至于我个人为什么参加了这次会谈,我想只是由于两点,第一,我参加广东军民工作(或军事工作)较早,第二,我与闻贺部的军事较早(因我与周逸群同志的特殊私人关系),若论在党、政、军三方面的名义职务,我感觉都不甚够资格。
但是实际上这次会谈我是在场的,而且感觉是“事关重要”,那是因为当时谈的是有关改变旗号、明确政治路线问题。这一问题当南昌起义本已在客观实际上发生,但是总没有好好的研究讨论,即“土地革命”,“党所领导的政权的建立”,“自力更生和国际援助”等具体办法。这些重要问题,两月来应当是经常思考的,而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方针下一直没有提出,而且沿途一直没有好好作过党和群众工作,似乎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到海口,等外援”上。这样重要的问题,一直到流沙才正式提出,而与比较多的人见面(譬如贺龙同志,在瑞金时加入廖乾吾同志和我)。
这一问题之所以可能提出,我想(因为我不明实际情况,只能推测)是和张泰来(即张太雷)同志于我们离汕头前恰到汕头有关。也可能离汕头而转进海丰的决定,正是因为张泰来同志偕苏联同志(究竟是苏联人或是其他国籍的第三国际代表我也不明,名字我也不知,只在他和泰来同志与贺龙同志见面时我也在场看见)到汕头方才决定的。因为这一撤离汕头的决定实在是仓猝得很,以至沿途行军宿营等等和沿途联系等项,据我所知均无甚准备,甚至沿途侦察等事也没有怎样进行——个人所知如此,究竟有没有,我也不很明白,因为我没有参加具体军事工作,我也不很熟习这一工作。
张泰来和那位外国同志好象并没有随军离汕,而是直接由汕转香港,因为我记得流沙会谈中并没有他们参加,而李立三同志之要去上海负中央重要工作责任应是张泰来同志传达的。因为流沙会谈当时,形式上好象是立三同志主持,并且他告知大家要去上海。
会谈地点好象是流沙村中(流沙当时似是一小村,记得似乎只一条不很长的街道,连镇市也说不上)中段一座坐北朝南的农村普通房屋。我们是在一农村房屋吃饭休息,只占用一间小堂屋,中是放一农村木方桌,再旁有临时搭成的两张木板床即坐着吃饭也供饭后稍息,以外余地就不多,因此并不能容多少人。堂屋外是一小天井,天井往南,就是门楼,都很小,完全是农村小房屋,也不过可容少数几人站立。堂屋两旁住屋锁着,门没有开,我们也没有进去。可知此次会谈并不是预先准备的,更不是成规模的会议,行军途上也不许可如此,而且我们通知是当日到葵潭宿营,原不准备在流沙多耽误时间,因此也不可以有时间从事讨论这样的大问题,只不过是由可能代表党的重要人员向负军事工作重要责任的少数同志传达一下党中央政策重要之点而已。
南昌起义时党原有一前敌委员会主持其事,但并没有公开,至少我不甚知道。这事现时可能只有周恩来和李立三两同志最明白,谭平山应明白,但已死多年无从质证,事实上人数很少,而张国焘代表党中央参加其间。张泰来到汕头第一步应即是向“前委”传达中央意旨,具体作法可能是到海陆丰再肯定,在流沙不过是初步传达于军事负责人作事先精神准备而已。因为当时前委有张国焘和谭平山参加其间,组织原不健全,离汕前张泰来匆匆传达也没有时间详细商讨这样重大问题并作出具体安排,因此在流沙就不能有妥当布置。会谈开始,只是由李立三(好象还有恽代英)说中央有新的重大决定,而李立三又说他要回上海工作。经过约莫半小时还没有说出要点,还是彭湃同志直截了当说出要进行土地革命,分田地,插红旗,而且马上动手。至于如何动手又没有说,当时大家无异议,也不能即时决定什么具体动手方案,彭湃同志本人也没有提出具体办法,不过经过一刻钟左右军队就要开始继续行军,会议即行结束,本来路上还可以继续谈,但时间已是下午三时左右,一出村口不远,前方即出现了情况,大家各归机关队伍,也就不可能再谈。
(二)起义军入普宁前后活动
就我个人所知,如前所述,由南昌到汕头原来希望是达到海口后即可得国际援助,作出以后行动决定。但九月二十四日到汕头后三日内,还没有消息(至少我个人不知道,大概是没有,如果有总会知道一些),以后即全军出发去汤坑前线,后方(汕头)空虚,一切建党、建政工作来不及开展,并且中间还在汕头发生了一次反革命暴动。我个人因为担负着一个全新而无经验、无准备的留守职务,几乎是在演空城计,近于赤手空拳,忙乱莫名,不知党政群众方面详细工作。我那时是二十五、六岁,只要能守住机关,守住汕头,已经算是尽了我的全力,这当然也借周恩来和周逸群帮助(周恩来同志在汕头,逸群同志在潮州,恩来同志主持党中央军委约莫有卫队十人、八人,逸群同志率千余人守潮州,有约莫二、三百人号称一营来往潮汕协防,如是而已),算是在任职三、五天内竟能渡过反革命暴动难关,安全离汕,现时回想已竭尽我当时所有力量,因为我和贺部职员原一无关系,从南昌起我只有一随行勤务员,既无枪枝,也无其他军用品(如望远镜之类),又不参加其它机关工作,突然参加这一重责,现时回想也觉莫明其妙,所恃唯党,而当时情况又殊觉微妙。
“前委”人数约不满十人(包括张国焘在内)。张深居简出,不接近群众,颇觉神秘。谭平山为南昌起义事与张国焘矛盾甚大,沿途随贺部行军,少有活动,也无多见解。李立三似担任政治保卫工作,沿途也不见有何表现,但沿途总算无事。比较深知潮汕和东江一带情况的应只有周恩来和彭湃二位。潭平山为人虽曾在广东负党重任,实极颟顸,彭湃同志以海陆丰农运知名,但对整个东江情况如何,本人不知其究竟,唯有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东征时任党政军重责,先后在东江约近一年,因此党群工作除周恩来同志外,唯恃彭
拜。李立三历任全国工运,对广东海员宜有所知,但未知在汕有何表现。其他随行粤人,如彭泽民系党外人士,叶挺等军人忙于军事,因此东江群运与党的工作,个人推想,唯周恩来同志与彭湃同志能于当时情况有所知,而彭湃早死,现唯周恩来同志可能有所回忆,但忙工作,亦不易见面,唯有通过党的途径,看能挤出时间谈出或写出片断或整段材料否。
个人所知(也是一两年内方才知道)义军到汕头后,周恩来同志曾派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同志刘立道到海陆丰取款若干万元供汕头方面需用。刘立道来往海陆丰与汕头之间当然经过普宁。而且据当时在海陆丰负部分责任的黄雍(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住北京)说:当时刘立道坚持要现洋,任何钞票不要,港币外币均不收,只好派出大量挑夫由海陆丰根据地运汕。当军队到达流沙时,银挑恰好也到达。我当时确曾看见一部分银挑到达贺部,并启箱分配。可见当时普宁应有相当联系,但十月一日下午何以在流沙竟出现突如其来的敌人部队,此种敌情究系何种部队,象正式广东方面反动军队抑系地方反动民团地主武装,似至现时尚未明了,如果当日地方党群工作良好。当然不至临时仓猝应战。
然本人于战后(即流沙遭遇战当夜)路过一祠庙,遇青年及三数老农民(中一人似为青年之母或祖母)正在夜谈,对我的态度极为良好。这青年竟称我军为我们的军队,并为我们带路,通夜步行,为我们作好各种准备,可见当地人民对我们极为接近。这青年似为一青年学生,对农民关系很好。当夜遇见地点距流沙南不过十里、八里,其姓名已不能记忆。现时回想,仍觉当地人民可爱。
陈公培
于北京西黄城根22号宿舍79号房
(原件见普宁县人民委员会修志会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普宁人民的革命斗争史料》。转抄自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起义资料》"
上一页
下一页
上一页:
下一页: